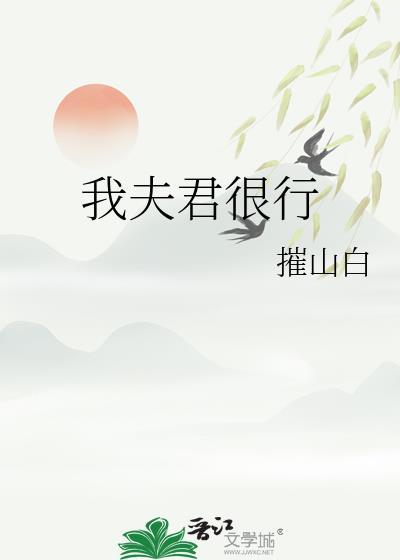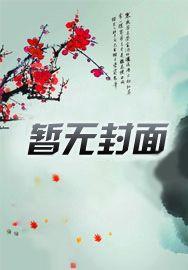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4章 枢纽理解中国三千年脉络(第1页)
第章《枢纽》理解中国三年脉络
从重庆火锅到北京炸酱面:我的味觉里,藏着怎样的中国?
上周六清晨,我在厨房煮重庆小面,红油刚滚,花椒的麻香就飘满了屋子。娃儿凑过来问:“妈妈,为什么姥姥寄的辣椒,比市买的香那么多?”我戳了戳她的额头:“馋猫!”
突然想起二十几年前在重庆老家,我的外婆也是这样在灶台前忙碌,山城的雾气裹着辣椒香,是我对“家”最早的记忆。
后来嫁到北京,第一次跟着先生去胡同里吃炸酱面,老板拿着长筷子搅着酱,说“咱老北京的酱,得用五花肉煸透,搁葱花儿才香”。我捧着粗瓷碗,嚼着筋道的面条,看着胡同里晒太阳的老人、追跑的孩子,又觉得这种踏实的烟火气,也是“家”的味道。可有时候夜深了,我会对着窗外的北京夜景呆:为什么我既想念重庆火锅的热辣,也离不开北京炸酱面的醇厚?为什么听到川剧的高腔会眼眶热,看到故宫的红墙也会心生敬畏?这种说不清的牵挂,像两根绳子,一头拴着长江边的山城,一头系着永定河畔的京城,让我忍不住琢磨:我脚下这两片截然不同的土地,到底怎么都成了“我的中国”?
小时候在重庆,总爱跟着外婆去磁器口赶场,石板路上满是陈麻花的甜香、火锅底料的醇厚,挑着担子的小贩喊着“担担面——”,声音能绕着吊脚楼转三圈。那时候我以为,中国就是爬坡上坎的山城,是嘉陵江与长江交汇的壮阔,是夏天坐在黄葛树下吃凉糕的惬意。直到十八岁第一次来北京上学,坐火车穿过华北平原,看到一望无际的麦田在风里翻涌,像金色的海浪,才突然现,原来中国不只有高低错落的山城,还有一马平川的平原;不只有热辣的火锅,还有温润的豆汁儿。
结婚后跟着先生去他姑姑河北老家,看到村里的老人用镰刀割麦子,汗水滴在土里,却笑着说“今年收成好,能多换点钱给孙子买书本”。那一刻我想起重庆老家种柑橘的舅舅,每年冬天踩着泥泞去果园摘橙子,冻得手通红,也总说“多卖点,给闺女凑学费”。两个老人,一个在华北平原种麦子,一个在四川盆地种柑橘,说的话不一样,干的活不一样,可那份对生活的踏实劲儿、对家人的牵挂,却一模一样。那时候我隐约觉得,或许“中国”不是某个固定的样子,而是这些不同土地上,相似的生活与相似的爱。
直到我翻开《枢纽》这部让我从中了解到中国三千年脉络的书,我才真正把这种模糊的感觉,变成了清晰的认知。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不是书本里那些复杂的理论,而是它像一个懂生活懂浪漫的朋友,用我们能摸得着的日常,读得懂的生活,讲透了中国的脉络。它说,中国从来不是一块整齐划一的土地,而是山与河、平原与盆地共同“拼”出来的家——就像我理解的重庆的山塑造了热辣爽朗的性格,北京的平原孕育了包容大气的气度,这些不同,从来不是分开的理由,而是凑在一起才完整的“家底”。
书里有句话让我反复琢磨:“历史不光是过去的镜子也是未来的镜子,理解中国三千年脉络,是为了看清我们在时空中的坐标”。以前我总觉得,“理解中国”是很宏大的事,跟我每天煮面、接送孩子没关系。可现在才明白,我对重庆与北京的双重牵挂,对火锅与炸酱面的同等热爱,其实就是“中国”最真实的样子。我的外婆在重庆种辣椒,先生的爷爷在河北种麦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连着这片土地的过去与现在。就像书里没明说的那样:所谓“精神故乡”,从来不是某一个地方,而是你走过的每一寸土地,吃过的每一口饭,藏在你骨子里的、对这片土地的牵挂。
可我还是有个疑问:重庆的山那么陡,北京的路那么平,南北的风俗差那么多,为什么我们依然会觉得“我们是一家人”?这种能把不同凑成“整体”的力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枢纽》里一定藏着答案,只是需要我慢慢往下读,从那些与我生活相关的细节里,一点点找出来——毕竟,我的故事里有重庆与北京,而中国的故事,本就是无数个“我的故事”凑起来的。
长城内外:中原沃土上,为何长出了“大一统”的根?
去年冬天去八达岭长城,站在垛口前往下望,北边的风裹着枯草味儿刮过来,带着股野劲儿;往南看,山脚下是整整齐齐的农田,哪怕是冬天,田埂也还留着笔直的轮廓,像谁用尺子画出来的。导游说,这道长城不光是砖石堆的墙,更是一条“看不见的线”——oo毫米等降水量线就跟着它走,线南边雨多,能种麦子、稻子;线北边雨少,只能长草,养牛羊。那时候我才突然懂,不是古人故意要修一道墙把土地分开,是这片土地自己,早就用雨水划好了农耕和游牧的边界。
想起小时候在重庆老家,跟着外婆去乡下走亲戚,路过一片稻田,田埂之间留着窄窄的小路,走上去一步都不能错,不然就会踩坏秧苗。外婆说:“种地就得有种地的规矩,哪块田种稻子,哪块田种油菜,啥时候播种,啥时候收割,都得按时候来,乱不得。”后来到了北京,去郊区朋友家玩,看到他们种小麦,麦田也是方方正正的,朋友的父亲拿着锄头,一点点把田埂修齐,说“田埂直了,浇水才匀,麦子才能长得一样好”。那时候没多想,现在才明白,中原的农耕文明,打从根上就带着“规矩”二字——你要守着土地过日子,就得按土地的脾气来,一分一毫都不能差。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这种“守规矩”,最明显的就是村里的祭祀仪式。前几年回重庆乡下,赶上村里的祠堂祭祖,整个村子的人都回来了,男人们穿着整洁的衣服,女人们端着准备好的祭品,孩子们跟在后面,安安静静的。祠堂里挂着祖先的牌位,老人站在前面,一字一句地念着祭文,讲着祖先当年开垦土地、养活一家人的故事。祭完祖,大家按辈分坐下来吃饭,谁坐主位,谁先动筷子,都有讲究。朋友说,他们北京郊区的村子也这样,逢年过节祭祖,族里的人聚在一起,不光是拜祖先,也是商量村里的事,比如谁家的地该修水渠了,谁家的孩子该上学了,大家一起想办法。
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儒家讲的“礼”。它不是书本上那些绕口的道理,是藏在种地、祭祖、吃饭里的规矩——因为大家都守着一块地过日子,要一起修水渠、防灾害,就得有秩序,有辈分,有互相帮衬的规矩。就像祠堂里的牌位,不光是纪念祖先,更是告诉所有人:我们是一家人,是靠着这块地、这些规矩,一代代活下来的。族田也是这样,留一块公田,收成用来帮衬族里的穷人,或者供孩子读书,这就是“礼”的实在用处——让定居在土地上的人,能抱团过日子,把日子过得安稳长久。
可长城北边就不一样了。之前看纪录片,草原上的牧民,跟着牛羊走,哪里的草好就去哪里,今天在这片草原搭蒙古包,明天可能就搬到几十里外的另一片草原。他们没有固定的祠堂,没有不变的田埂,生活里充满了流动和变化。你没法跟牧民说“按辈分坐”,因为他们的日子不是围着土地转的;你也没法跟他们说“守着一块地过日子”,因为草原的草不会一直长在一个地方。所以草原文明里,没有中原这样的“礼治”,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法则,比如更看重勇气和力量,因为要应对风沙、应对迁徙中的危险。
这时候再看长城,就明白它不只是一道军事防线,更是“礼”的边界。长城以南,人们守着土地,守着祠堂和族田,守着“礼”带来的秩序和安稳;长城以北,人们跟着草原走,跟着牛羊走,带着风沙里的自由和不羁。就像那句话说的:“长城以南,种下的是粮食,也是世代不变的伦理;长城以北,吹过的是风沙,也是自由不羁的灵魂。”这不是谁好谁坏,是两片土地,长出了两种不一样的活法。
而中原人对“安稳”的渴望,早就刻进骨子里了。每年春节,不管在外地打工多远,大家都要往家里赶,哪怕要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哪怕路上再挤,也要回到老家,跟家人一起吃顿年夜饭。我身边的朋友,不管是重庆的还是北京的,都这样——重庆的朋友说,过年要回老房子,贴春联,跟父母一起包抄手;北京的朋友说,过年要回郊区老家,跟兄弟姐妹一起给长辈拜年,吃妈妈做的炖肉。这就是“落叶归根”,是不管走多远,都想回到自己的“根”上,回到那个有秩序、有牵挂的地方。
以前总觉得,“大一统”是皇帝们的野心,是他们想把更多的土地抓在手里。可看了《枢纽》才明白,根本不是这样。中原的平原那么大,土地那么肥沃,要种好庄稼,就得修水渠、防洪水,这些事不是一家一户能做到的——你家的地在下游,我家的地在上游,要是不一起商量着修水渠,上游的水多了会淹了下游,上游的水少了下游又会旱。还有遇到灾害的时候,比如蝗虫来了,或者大水了,只有大家抱成一团,才能扛过去。所以“大一统”不是谁逼出来的,是这片平原沃土注定的——你要在这片土地上好好过日子,就得有一个能把所有人组织起来的“大集体”,就得有统一的规矩和秩序。就像种麦子,你得把土地整平,把种子撒匀,才能长出一片好麦田;中原的农耕文明,也注定要长出“集权”的秩序,才能让所有人都安稳地活下去。
现在再想那些村里的祭祀仪式,想春节回家的路,突然就懂了:儒家的“礼”,不是束缚人的条条框框,是祖先们传下来的“生存智慧”——它让定居在土地上的人,知道该怎么互相帮衬,怎么守住自己的根,怎么把日子一代代传下去。而“大一统”,也不是冰冷的权力,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为了守住“安稳”,一起做的一场大型合作实验。
可我又忍不住想:既然农耕文明这么需要“秩序”,那当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越过长城,来到中原的时候,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活法,又会撞出怎样的火花?中原的“礼”,能容得下草原的“自由”吗?或许,这就是《枢纽》接下来要告诉我们的,关于中国文明融合的秘密。
草原——游牧者的激情与部落联盟的崛起
马蹄声是草原的脉搏。
不是中原驿道上“得得得”的规整节奏,也不是城门口骡马驮货的沉闷声响,草原上的马蹄声带着风的形状,有时轻得像掠过草尖的蝶翼,有时重得能震落岩石上的霜花。清晨天还没亮,当第一缕微光刚染亮东方的地平线,马蹄声就醒了——牧人勒着缰绳,马群踩着露水往水草丰美的地方走,蹄子踏过沾着霜的草叶,“沙沙”声混着马的响鼻,在空旷的草原上飘出老远。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这声音里藏着游牧者的日子。他们没有像中原那样“钉”在土地上的家,蒙古包拆了又搭,跟着牛羊走,哪里的草绿、水甜,哪里就是家。我曾在纪录片里看到,一户牧民搬家时,男人骑着马在前头引路,女人坐在勒勒车上,车辙压过草原,像给大地画了道临时的线。孩子们趴在车上,手里攥着刚摘的野花,看着身后的蒙古包越来越小,直到变成草原上的一个小黑点。马蹄声一路跟着,有时候慢,有时候快——遇到好草甸子,马会放慢脚步,好像也在享受嘴里的嫩草;要是天快黑了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马蹄声就变得急促,像在跟太阳赛跑。
可这流动的日子,从来都不是诗里写的那样轻松。草原的浪漫背后,藏着最直接的残酷。比如“白毛风”来的时候,那是草原最吓人的脾气——风裹着雪粒子,像无数把小刀子刮在脸上,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连方向都分不清。这时候,马蹄声就变了味,不再是悠闲的“沙沙”声,而是慌乱的“哒哒”声。牧人要赶着牛羊往避风的山坳里跑,马在风雪里睁不开眼,只能凭着本能往前走,蹄子有时候会陷进雪窟窿里,拔出来的时候,雪沫子顺着马腿往下掉。有一次,纪录片里的老牧人说,他年轻时遇到过一次白毛风,为了护住羊群,他和马在风雪里走了整整一天一夜,马的蹄子都磨破了,血染红了雪。最后找到避风处时,马累得跪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那时候他才知道,草原上的每一步,都是用命换的。
但草原也有热闹的时候,比如那达慕大会。这时候,马蹄声里全是豪情。摔跤手们穿着皮甲,骑着马在草原上转圈,马跑得又快又稳,蹄子踏在地上,“咚咚”的声音像打鼓。射箭的选手趴在马背上,拉弓的时候,马会突然停下来,蹄子轻轻刨着土,好像也在为选手鼓劲。孩子们围着赛马的场地跑,手里拿着奶豆腐,嘴里喊着“加油”,马蹄声、欢呼声、马头琴声混在一起,把草原的热闹推到了顶点。老人们坐在蒙古包前,喝着奶茶,看着年轻人撒欢,脸上的皱纹里都带着笑——他们知道,这热闹里藏着草原的精气神,是游牧者对生活的热爱,也是对艰苦日子的反抗。
可这样的日子,也会被远方的变化打乱。就像中原人要守着土地过日子一样,游牧者也得靠着和中原的贸易活下去——他们有上好的皮毛、马匹,需要中原的粮食、茶叶、盐。以前,小部落们各过各的日子,春天去边境的互市上换点粮食,冬天就躲在山坳里过冬,倒也安稳。但当中原统一成一个大帝国后,事情就变了——有时候,中原的皇帝会关上边境的门,不让贸易做了。这时候,小部落们就慌了——没有粮食,冬天怎么过?没有茶叶,牧人们的肚子会胀气,连马都没力气跑。
就像现代商场里的小公司,平时各做各的生意,日子还能过;可一旦遇到大集团垄断市场,小公司就只能抱团取暖。草原上的小部落们也是这样,贸易一断,生存就成了问题。单个部落的力量太小,去跟中原谈判,人家根本不理;想自己种粮食,草原的土地又长不出好庄稼。这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说:“我们得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部落,才有力量。”
成吉思汗就是这样站出来的。那时候,草原上有几十个小部落,你打我,我打你,像一盘散沙。成吉思汗年轻时,父亲被别的部落杀了,他带着母亲和弟弟们躲在山里,靠挖野菜、捉兔子过日子。他知道,单个部落的脆弱——要是遇到别的部落抢东西,只能眼睁睁看着;要是冬天没粮食,只能等着饿死。后来,他开始联合周围的小部落,跟他们说:“我们合在一起,就能去跟中原要贸易,就能不再受欺负。”一开始,没人相信他,觉得一个年轻人能做成什么事。可当成吉思汗带着自己的部落,打赢了几次抢粮食的战斗,把抢来的粮食分给大家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跟着他。
这像极了现代的团队合作——当外部有压力时,只有把分散的力量聚起来,才能做成大事。成吉思汗就像一个优秀的团队eader,他知道每个人需要什么:牧民们需要粮食、安全,部落领们需要荣誉、权力。他把大部落分成一个个小团队,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任务,有的负责放牧,有的负责打仗,有的负责跟其他部落谈判。就像现代公司里的部门分工,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慢慢的,草原上的小部落们都联合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
这时候,草原的马蹄声变了。不再是单个部落零散的“沙沙”声,而是成千上万匹马一起奔跑的“轰隆隆”声,像草原上的雷声,能震得大地都在抖。当这个大部落的人再去边境时,中原的官员不敢再随便关门了——他们知道,这不再是一群好欺负的小牧民,而是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大联盟。贸易重新开始,牧人们又能换到粮食、茶叶,冬天再也不用怕饿肚子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有人说,草原没有围墙,游牧者的国界在马背上。这话一点都没错。中原人用砖石砌长城,把自己圈在里面,追求安稳;游牧者骑着马,把整个草原当成家,哪里有草,哪里就是国界。他们不需要固定的房子,不需要整齐的田埂,因为他们的家在马背上,在流动的日子里。这种自由,是中原人很难想象的——中原人一辈子守着一块地,从生到死都在一个村子里;而游牧者,一辈子能走几千里路,能看到不同的草原、不同的山。
可这种自由,不是“躺平”。现在很多年轻人纠结“躺平”还是“奋斗”,觉得躺平就是轻松,奋斗就是辛苦。但草原的游牧者告诉我们,自由和奋斗从来不是对立的——他们的自由,是靠马背上的奋斗换来的。为了找到好草甸子,他们要每天走几十里路;为了抵御白毛风,他们要和风雪搏斗;为了保护牛羊,他们要和狼群对抗。他们的自由,是“能在草原上活下去”的自由,是“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自由,这种自由里,藏着最硬核的奋斗。
就像老牧人说的:“草原不会白给你东西,你要跑,要拼,才能拿到。”他们不像中原人那样,有固定的土地可以依靠,他们的依靠只有自己的马、自己的力气、自己的智慧。遇到困难时,他们不会想着“躺平”,因为躺平就意味着饿死、冻死。他们只能站起来,骑着马,去寻找新的水草,去对抗危险——这不是被迫的奋斗,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生存智慧。
现在的人,总喜欢计划未来,觉得只有把一切都安排好,才能安稳。可草原的游牧者告诉我们,有时候,适应力比计划更重要。草原的天气说变就变,可能早上还是晴天,中午就下起了雨;可能今天还在这片草甸子,明天草就被牛羊吃完了。他们从来不会计划“下个月要在哪个地方放牧”,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他们能做的,就是跟着变化走——天气变了,就找避风的地方;草没了,就去下一个地方。这种适应力,在现在这个快变化的时代,反而显得格外珍贵。
比如职场上的人,有时候会遇到公司裁员、行业变化,这时候,很多人会焦虑,会觉得自己的计划被打乱了。可如果学学草原的游牧者,就会明白,变化不是坏事——就像草原的草吃完了,就去新的地方,那里可能有更肥美的草。职场上遇到变化,也可以去学新的技能,去尝试新的工作,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机会。草原上的马,不会因为路变了就停下脚步;人也不该因为环境变了,就放弃前进。
草原的魅力,从来都不是它的辽阔,而是它教会人的生存哲学——在流动中寻找安稳,在自由中学会奋斗,在变化中保持适应。就像那句金句说的:“中原用粮食砌墙,草原用风沙铸剑;一个追求永恒的稳定,一个信仰流动的生存。”这两种活法,没有谁好谁坏,都是这片土地给人的礼物。
当夕阳西下,草原被染成金色时,马蹄声又变得慢了。牧人赶着牛羊回蒙古包,马的蹄子踏过夕阳下的草叶,留下一串长长的影子。蒙古包里,奶茶已经煮好了,香气飘在草原上。这时候,你会明白,草原的激情不是一直奔跑,而是在奔跑之后,能有一个温暖的蒙古包;游牧者的韧性,不是永远战斗,而是在战斗之后,还能笑着喝上一碗热奶茶。
而那些马蹄声,就像草原的记忆,记着游牧者的苦,也记着他们的甜;记着他们的孤独,也记着他们的热闹;记着他们的过去,也记着他们的未来。当这些马蹄声汇聚在一起,就成了草原帝国崛起的声音,成了游牧者对抗命运的声音,也成了人类在艰苦环境中,依然能活出精彩的声音。
过渡地带——二元治理的智慧
站在山海关城楼上往南望,是中原一望无际的麦田,田埂笔直得像用墨线弹过,农舍的烟囱里飘着炊烟,风里都带着麦香;往北看,是东北黑土地延伸向草原的过渡带,地里种着玉米和大豆,远处的山坡上还能看到几群牛羊,偶尔有萨满祭坛的彩色经幡在风里飘——这就是过渡地带的样子,既不是纯粹的农耕,也不是纯粹的游牧,像一杯掺了奶的茶,两种味道融在一起,却又各自分明。
这里的土地是“混血”的。东北的辽河平原,春天里,汉人农民会扛着锄头去地里种高粱,田埂边可能就立着一块萨满教的“神石”,石头上刻着看不懂的符号,是当地满族或蒙古族人为了祈求风调雨顺立的。到了秋天,收割完庄稼,汉人会去祠堂祭祖,供桌上摆着馒头和米酒;而少数民族则会在萨满的带领下,围着篝火跳神,鼓声和歌声能传到几里外的村子。我曾在辽宁的一个小村子里见过这样的场景:村东头的祠堂里,汉人正在给祖先磕头;村西头的空地上,满族老人正用满语唱着古老的歌谣,孩子们围着篝火跑,手里拿着汉人做的糖人。没有人觉得奇怪,好像这样的“混搭”本就该如此——就像地里既种着中原的庄稼,也长着草原的牧草;人们既过春节,也过那达慕,两种生活方式像两条河,在这里汇在了一起。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斗罗妓院佚
- 从纲手大人开始,将木叶的忍者们都催眠改造成忠于吾等胯下的肥奶肉臀の弱智母猪!琴
- 斗罗大陆之催眠武魂玖
- 精灵宝可梦 怀孕 收服!通通沦为小主人的受孕母猪吧原
- 幼儿园里的黑人小鬼同学,把可爱的黑丝吊带肥臀妈妈爆插到恶堕叫爹!(无绿改)珍
- 原神:全女婚后,我开始过上性福生活墨
- 斗罗大陆之双生淫魂未
- 原神众女涩涩风
- 后崩坏书强
- 传承淫神技能后穿越到斗罗大陆世界莉
- 从斗罗开始收取性奴的诸天之旅lgcloveself
- 崩坏三之精厕女武神王
- 崩坏:性穹铁道(星穹铁道改写)稚柒七仁
- 斗罗之绝世唐门猎美王乌
- 原神即堕赤
- 原神 可以色色!瞳
- 斗罗大陆:龙魂之欲x
- 崩坏:性穹铁道(星穹铁道改写)稚
- 原神NTR叶
- 斗罗大陆—永恒的炮友零
- 斗罗大陆2绝世唐门足交传说hyh
- 崩坏:性穹铁道tiny
- 关于提瓦特里所有女孩子都喜欢肛交这件事M
- 斗罗之我的武魂是√8f
- 斗罗绝世,世界调制模式语灵零
- 莹妹和她的婊子伙伴们硝
- 后宫催眠日记十
- 从纲手大人开始,将木叶的忍者们都催眠改造成忠于吾等胯下的肥奶肉臀の弱智母猪!琴
- 将警花妈妈调教成丝袜孕奴佚
- 原神NTR叶茗
- 斗罗妓院佚
- 全家肉便器系统零
- 超神学院 高冷骄傲清纯艳丽各色顶级女神暗中纷纷被调教成为了沉迷主人大肉棒的小狗性奴母猪烈
- 原神的女角色们总会向旅行者露出小穴的,对吗罗
- 斗罗淫传:肉棒是三美神祇唯一信仰,子宫只为承纳我的精液而存在佚名
- 斗罗淫魂z
- 少年的熟女天国b4204812
- 传承淫神技能后穿越到斗罗大陆世界莉
- 原神 纯粹涩涩瞳
- 原神:提瓦特猎批王亦
- 把媚黑婊骚鸡女武神都淫堕自己的专属肉便器沐
- 我被隐奸NTR的绿帽全家桶和萝莉家族守护神PM4949
- 从斗罗开始收取性奴的诸天之旅lgcloveself
- 阴险的洗脑调教女武神全员肉便器化计划黑
- 穿越到原神获得催眠系统,攻略各位美少女开后宫的故事十
- 仙子破道曲漆黑烈焰使
- 日在崩坏葉
- 斗罗:娇艳人妻小舞和女儿恶堕成肥猪的孕奴雪
- 星穹铁道老婆全图鉴调教收集计划CYY
- 掌握催眠之力后的淫乱生活蘑
- (综漫同人)【综漫】带着衣柜去打工综漫七夜琉
- 警门赘婿写书还债
- 无极仙尊:从废物赘婿逆袭开始爱码字的猫
- 拿山海经当菜单,凶神天天求喂饱暴君不早朝
- 千秋世家:从秦末开始道之起源
- 资本家小 姐觉醒后,手撕仇人海岛随军暖暖的小时光
- 陆总,太太说她丧偶回归豪门了兰舟
- 剑来:开局垂钓骊珠洞天夏雨秋风
- 废土:恶毒养母带崽吃香喝辣重鸣谷
- 表姑娘拒绝偏执世子后,被抵墙角了+番外晓棠
- 海岛来了个娇小 姐,军长他心慌慌临临
- 听懂动物心声后,全世界毛绒绒集体红温梅归隐
- 三岁小禾宝,把全家哭进侯府狷介
- 表姑娘出嫁后,被疯批权臣强取豪夺峤衡
- 转世后:宿敌成了我的白月光烟羽舟
- 七零,我打猎养资本家大小姐老婆六月的狼
- 被扫地出门后,转身高嫁千亿大佬超级大兔子
- 鬼灭之刃:从苇名来斩断不死骑猪北下
- 开局王府世子,最终摆烂失败西蜀小胖
- 小姐,姑爷又摆烂了饭抄鸡蛋
- 皇后娘娘养娃实录(清穿)桃纤纤
- 木古里故事莫然岚山
- 捡漏儿:从文玩小贩到古玩大亨披雪楼主
- 我伯父是康熙大司空
- 团宠萌崽:皇城毛茸茸全是我线人就是不白
- 爹爹先别死:神医萌宝流放救全家伍拾一
- 退婚掀桌!商小 姐掏空渣总家产了绘绘
- 长生珏+番外听酒
- 黄金万两CP+番外向江梧桐
- 世界末日,系统让我准备高考灵陌紫钰轩
- 全民求生:开局组队双胞胎姐妹遗梦三岁
- 财富自由:从三十开始静候轮回
- 难养顾九绿
- 人性的那些事儿蹦蹦跳的小鲤鱼
- 骁英谨书·壹曈穆
- 闺蜜变婆媳?俩寡妇联手制霸八零+番外秋江冷
- 病房流产时,渣总在陪白月光度假海钓嘟嘟宝
- 海岛来了个娇小 姐,军长他心慌慌临临
- 抄家夜觉醒,八岁奶团撕圣旨救侯府九月花
- 机长请降落我心间+番外落珠


![从海棠市逃出来的男人/要你寡[穿书]](/img/2360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