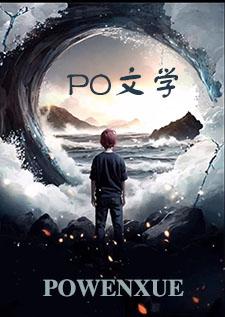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0章 捡到个美人h(第1页)
桃林深处,暖风醺人。
元晏憋了一肚子气,在桃花林里漫无目的地游荡。
绯红的花瓣成团成簇地砸下来,落在肩头、梢,沉甸甸的。过分浓烈的甜香,熏得她头昏脑胀。
如果不是因为云澈,如果不是为了那点渺茫的线索……她真想现在就收拾东西一走了之,省得在这里看人脸色,受人嫌弃。
脚下的花瓣积了厚厚一层,踩上去绵软无声,只挤出更腻人的香气。心里那团火还在烧,烧得眼眶涩,烧得胸口闷,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她算什么呢?
对云澈而言,她又究竟算什么?
随手拨开眼前缀满花苞的枝条,纷纷扬扬的花雨劈头盖脸砸下来,糊了满头满脸,她也懒得去拂。
花雨深处,一个身影倚着琴案,似乎正在昏睡。
是个少年。
墨如瀑,披散在肩头。几缕丝落在脸颊,暖风轻轻拂过,梢随着气流极轻微地颤动,在他脸上投下细碎的、摇曳的阴影。
他的皮肤白得惊人,是那种久不见天光的冷白,像深埋地底千年都不曾被人触碰过的上好羊脂玉。
可他的唇色却极其浓艳,应该是将整朵红梅揉碎了,只将最艳的一滴汁水点染其上。
毫无防备的漂亮,赤裸裸地摊开在这片灼热的桃色里。
元晏的心莫名跳快一拍。
脑中掠过一些模糊的片段,似乎在很久以前,她也曾看过这样一个人。
是谁?
她努力回想,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血迹,伤口,微弱的呼吸……
还有将那人背起时,触到的寒意。
鬼使神差地,元晏走上前。
少年双目紧闭,呼吸轻浅,脆弱得不堪一击。
她蹲下身,将他背起。
他比她想象中要轻得多,瘦削的身体贴着她的背脊,感觉不到什么重量。
她将他带回了云澈小院的厢房,让他平躺在床榻上。
得看看有没有伤。
她这样想着,手指搭上他衣襟的系带,稍一用力,看起来挺复杂的结就散开了。
外衫滑落,中衣散乱。
并不是她预想中的削瘦孱弱。
少年不算健壮,但肌肉线条很漂亮,宽肩窄臀,腰腹收得很紧,没有一丝多余,每一寸都恰到好处。
元晏的手不由自主地抚上他平坦紧实的小腹。
掌下,丹田处,一团凝练圆融、生生不息的气感正在平稳运转。
是金丹。
金丹期?
这个看起来不过弱冠的少年,竟已结丹?
天玄宗的天才已经多到这种地步了吗?随便捡到一个昏迷的少年,都是金丹期的修为?
“师娘尚在筑基……”
“若欲长久相伴师尊左右,还需在修行上多下苦功……”
“方不负师尊一片苦心。”
景澜那些鬼话又在她耳边嗡嗡不停。
真烦。
凭什么?
凭什么他可以一闭关了之,将她置于这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
凭什么他可以理所当然地评判她是否配得上云澈?
凭什么她就要在这里,对着这个来历不明、可能是谁派来试探她的美貌少年,反复掂量到底该不该救?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关于提瓦特里所有女孩子都喜欢肛交这件事M
- 传承淫神技能后穿越到斗罗大陆世界莉
- 掌握催眠之力后的淫乱生活蘑
- 斗罗大陆—永恒的炮友零
- 原神 可以色色!瞳
- 幼女天空下万恶我为首
- 原神 纯粹涩涩瞳
- 斗罗淫魂z
- 斗罗大陆之超级绿牛系统枫
- 日在崩坏葉
- 斗罗:流氓篇烈
- 淫魔化的提瓦特大陆此
- 崩坏:性穹铁道tiny
- 我的美艳警察妈妈丈八蛇矛
- 用肉棒武魂打通斗罗大陆!aleXeskandar
- 原神众女涩涩风秋火儿
- 原神NTR叶
- 全面崩坏!星穹铁道!S
- 豪乳老师刘艳tttjjj_200
- 穿越到原神获得催眠系统,攻略各位美少女开后宫的故事十
- 斗破苍穹-无尽的堕落助手
- 冲喜娘妻魔师
- 崩坏星怒铁道月
- 莹妹和她的婊子伙伴们硝
- 原神众女涩涩风
- 直播,然后碰瓷男主秉烟
- 如何阻止龙傲天干掉27个我松露桨
- 府上来个娇美人,阴鸷权臣强夺入帐巨兔唇下有颗痣
- 逆徒跪下!师尊摆烂后躺赢修仙界薯条果冻
- 聆听夏天的秘密它的猫
- 一刀破仙凡大清韵
- 四合院:火红年代享受生活恭禧发财
- 欲野垂星幻有纱雪
- 重生明末再造华夏飞星骑士2025
- 人在揍敌客,被迫养黑猫一鸽不鸽
- 从炮灰到主角,我在三千世界补位山药咕咕汤
- 刚卷成高考状元,系统就让我躺平小鸡球球
- 老公死了,呜呜,我装的橘铃
- 玫瑰栽培手册噫吁嚱鸭
- 论吻戏借位的正确姿势[娱乐圈]姜宜非
- 世界纪元:次元直播间之不屈之歌天启阿克与黑木介一
- 寡妇娘子要寻夫白玉苏苏
- 四合院:掏空全院,贾家卖子求荣爱吃椒盐大虾的岳寒冬
- 错撩温良书生后卧扇猫
- 猫妖在立海大艰难求生最好吃的朋友
- 开局流放?星际顶级大佬求我抚慰木汐木汐
- 从一纸金章到人间真仙白云泡泡
- 香山浔风应雨竹
- 懂爱王乐诚
- 我,财神爷,撒钱闫桔
- 仙骨至尊锋墨汁
- 错撩温良书生后卧扇猫
- 虞妖渡一朵心闲
- [娱乐圈]我真没有恋丑癖啊鹤八
- 天降双系统砸脸,我不无敌谁无敌米利欧12138
- 我们的妻主是特种兵小鲜儿
- 乔安安小吃店[美食]三海间
- 我不想当主角了水一天
- 从一纸金章到人间真仙白云泡泡
- 婚后余生一枚柚
- 穿越之:相公你醒了!泽基山人
- 你是独属于我的帕罗西汀琉玥雀雀
- 玫瑰栽培手册噫吁嚱鸭
- 一般路过普通人会收留幽灵公安吗?揭去安眠
- 聆听夏天的秘密它的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