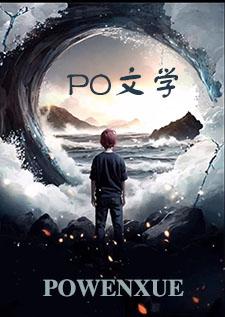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48章 单元4 富商诈尸案续(第3页)
这,便是第一章——王典史的刁难,老头的麻布,还有虎娃的糖画,共同织就的,是迷局的网,也是破局的刃。当张金彪的獬豸角断处指向马府灵堂,当醒魂草的苦香混着“瑞丧”的金粉,这场藏在丧宴里的谋杀,终将在断角与银线的共振里,露出最狰狞的面目,也终将在雪粒子的冲刷下,让每个被当作“祥瑞”祭品的灵魂,都能借着獬豸角的光,说出属于自己的、关于“人非瑞药”的真相。
《诡宴缉凶录·獬角破局》
第一卷·丧宴迷局
第二章:食盒里的针
顺天府衙的穿堂风卷着雪粒子灌进走廊,老王的烟袋锅子在袖口蹭出细密的油印,铜锅边缘的齿轮纹磕在廊柱上,发出细碎的响。他盯着张金彪腰间晃动的残角腰牌,忽然压低声音:“头儿,昨儿朱老说第七具骸骨的指甲缝里,除了金粉还有……”
“嘘——”张金彪忽然按住他的肩膀,目光扫过远处抬食盒的小厮。八人抬的朱漆食盒绘着獬豸衔草纹,独角缺处却用金箔贴成完整的角,与他腰间的断角形成刺眼的对比。大牛攥着冷窝头的手忽然顿住,口水滴在青砖上,却见食盒底部渗出的油迹,在雪地上洇成齿轮形状。
“都盯着点食盒,”张金彪摸向袖中藏的粗麻布,银线獬豸纹擦过掌心的月牙疤,“马府的‘瑞气蒸羊’用的是‘七合锅’,锅底刻着的齿轮纹,和死者锁骨的淤青一模一样。”他忽然想起昨夜在义庄,死者后颈的针孔边缘,隐约有圈极细的银线压痕——像极了食盒铜扣的纹路。
老王的烟袋锅子敲在廊柱上,火星溅进雪缝里:“头儿,您说王扒皮为啥非让咱盯马三公子?那小子昨儿在后厨待了半个时辰,出来时袖口沾着醒魂草汁——这草可是咱顺天府的‘禁药’。”他忽然指向食盒旁的小厮,对方袖口的蓝布补丁下,露出半截银镯,刻着
;“承恩”二字。
雪粒子忽然变大,砸在食盒的金箔上沙沙作响。大牛的冷窝头掉在地上,却顾不上捡——他看见抬食盒的小厮脚下一滑,食盒倾斜,露出里头白瓷碗的边缘,碗沿竟缠着圈细如发丝的银线,和张金彪飞鱼服补丁上的银线,出自同个绣坊。
“大牛,去帮小厮抬食盒,”张金彪忽然塞给他个醒魂草香囊,“盯着碗底的记号——七年前我爹查‘齿轮计划’时,用过同样的白瓷碗。”他忽然想起陈典簿的血书,第二页画着的食盒暗格,此刻在雪光下,竟与眼前的朱漆食盒,分毫不差。
食盒抬进马府二门时,张金彪趁机扫过盒盖内侧——用密陀僧画的齿轮与獬豸角,独角缺处标着“戌时七刻”。他忽然摸到腰间的残角腰牌,断角处的“张”字刻痕,与盒盖的獬豸角缺处,在风雪里形成一道无形的线,直指马府后院的柴房——那里飘出的烟,带着醒魂草被烘干的焦香。
“张旗牌,”马府管家皮笑肉不笑地递来碗“瑞气茶”,茶面上浮着的金箔,恰好盖住碗底的齿轮纹,“您弟兄们盯着点外院就行,内宅的‘祥瑞法事’,可不是常人能看的。”他袖口的齿轮纹绣线蹭过张金彪的飞鱼服,银线勾住补丁上的獬豸眼,竟在雪光下,让那双眼动了动。
老王忽然咳嗽起来,烟袋锅子敲在管家递来的茶碗上,火星溅进茶水里,竟腾起淡紫的烟——醒魂草遇火的征兆。张金彪望着管家骤然变色的脸,忽然想起老头说的“纸人手腕戴银镯”——此刻管家的左手腕,正戴着同样的银镯,刻着的“承恩堂”三字,被雪粒子盖住半边,竟成了“承思堂”。
“管家这银镯,倒是和城西李娘子亡夫的陪葬品很像,”张金彪忽然抓住对方手腕,银镯内侧的月牙形凹痕,恰好贴上他掌心的疤,“巧了,我爹娘的棺木里,也有只刻着‘獬角断’的银镯。”
雪粒子忽然灌进走廊,吹灭了廊下的灯笼。黑暗里,管家的银镯发出细不可闻的“咔嗒”声——镯身竟裂开两半,露出藏在夹层的银针,针尖刻着“王”字,与死者后颈的针孔,严丝合缝。大牛的惊呼声混着雪粒子落下:“头儿!食盒里的蒸羊……羊眼睛是真的!”
张金彪忽然推开管家,冲进后厨——朱漆食盒敞着盖,白瓷碗里的“瑞气蒸羊”淌着油汤,羊头的眼睛却被挖去,replacedby两枚银珠,珠面刻着“张承煜”的“承”字,缺笔处嵌着醒魂草的枯叶。他忽然想起七年前母亲的血衣,衣领处绣着的“醒”字,此刻在汤油里显形,竟与银珠的缺笔,拼成“醒承”二字。
“张旗牌好大的官威!”王典史的旱烟袋声从身后传来,火星在黑暗里明灭,“马府的‘祥瑞宴’也是你能闯的?当年你爹娘就是坏了‘祥瑞’的规矩,才落得……”
“落得被人用银针扎后颈,再塞进‘祥瑞棺’?”张金彪忽然转身,掌心的银针映着雪光,针尖的“王”字,与王典史旱烟袋锅子上的齿轮纹,在风雪里重叠,“王典史,您袖口的绣纹,和管家的银镯、死者的麻布,都是同个作坊的活儿吧?”
旱烟袋重重摔在地上,火星溅在食盒的金箔上,烧出个焦洞,却露出底下的密纹——齿轮中央刻着“王”字,周围环绕着十二具骸骨的轮廓,正中央的空缺处,画着株醒魂草,草尖指向的,是王典史的旱烟袋。老王忽然捡起烟袋,铜锅内侧刻着的“齿轮第七”,与义庄第七具棺木的记号,分毫不差。
雪停了,后厨的天窗漏进月光,照在张金彪的残角腰牌上——断角处的“张”字,此刻被羊油与醒魂草汁染成淡紫,竟在月光下,显出“醒”字的雏形。他忽然想起父亲藏在腰牌里的密信:“当食盒的金箔烧出焦洞,当银针的‘王’字指向旱烟袋,齿轮的第一颗铆钉,便该松了。”
大牛忽然指着羊头下的羊骨,骨缝里嵌着半块残布,经纬间的银线,正是老头攥着的粗麻布:“头儿!这羊骨上的齿痕,和第七具骸骨的一模一样——他们用死人骨头熬汤!”
王典史忽然狂笑,烟袋锅子砸向食盒,铜锅与白瓷碗相撞,发出刺耳的响:“张金彪,你以为破了个食盒就能救人?‘齿轮计划’的药引,从来都是活人的血、死人的骨!你爹娘当年想查,结果呢?”他忽然指向张金彪的腰牌,“獬豸角断了,就该知道什么叫‘祥瑞不可违’!”
月光穿过天窗,照在张金彪掌心的银针上,针尖的“王”字被醒魂草汁蚀去,竟显出“亡”字——那是死者们用骨血,在丹毒里刻下的“控诉”。他忽然将银针扎进食盒的金箔,银线獬豸纹与金箔的獬豸角共振,竟在地面映出完整的獬豸轮廓,角尖指向的,是马府后院的柴房——那里堆着的“祥瑞纸人”,手腕上的银镯,正发出细碎的“咔嗒”声。
这,便是第二章——食盒里的银针,羊骨上的齿痕,还有雪夜里的共振,共同织就的,是凶手的饵,也是破局的线。当张金彪的獬豸角断处指向食盒的密纹,当醒魂草的香混着人血的腥,这场藏在“喜丧”里的盛宴,终将在银针与骨血的碰撞里,露出最血腥的面目,也终将在月光的照耀下,让每个被熬进汤里的灵
;魂,都能借着獬豸角的光,喊出属于自己的、关于“人非食材”的怒吼。
《诡宴缉凶录·獬角破局》
第一卷·丧宴迷局
第三章:暗渠里的骨
顺天府衙的灯笼在风雪里晃成暖黄的团,张金彪指尖的牛皮图边角蹭着陈典簿的血渍,红笔圈着的“三进东厢”在雪光下泛着暗紫——那是小叫花子临终前,用冻僵的手指在他掌心画的圈。老王的烟袋锅子磕在廊柱上,火星溅在他飞鱼服的补丁上,银线獬豸纹被映得发亮:“头儿,您说那孩子死前攥着的醒魂草,为啥偏偏是七片叶子?”
“因为第七具棺木的死者,是他爹。”张金彪忽然扯开牛皮图,背面用密陀僧画着齿轮与獬豸角,独角缺处缠着七根草茎——每根茎上,都刻着个极小的“王”字。他忽然想起虎娃说的“纸人手腕戴银镯”,此刻牛皮图的暗纹里,银镯的轮廓正与齿轮中央的“王”字重叠,“大牛,把咱的‘规矩’亮出来——去马府后厨借个火,顺便盯着抬棺材的脚夫。”
大牛揉着饿扁的肚子,皂隶巾上的雪化成水,滴在牛皮图的“暗渠”二字上:“头儿,那蒸羊的香味……”话未说完,张金彪已将半块冷窝头塞进他手里,窝头里藏着片醒魂草——叶片边缘的锯齿,恰好能勾住马府地窖的齿轮锁。
戌时的马府老宅浸在深灰的暮色里,三进东厢的青石板下,暗渠的流水声混着雪粒子,敲出细碎的节奏。张金彪贴着墙根蹲下,指尖划过砖缝里的银线——和死者指缝的麻布、食盒的金箔一样,织着獬豸纹的暗码。老王的烟袋锅子忽然顿住,铜锅边缘的齿轮纹,竟与砖缝的银线严丝合缝:“头儿,这暗渠的砖,和义庄第七具棺木的底板,是同个窑口的。”
雪粒子灌进领口,张金彪展开牛皮图,红笔圈住的“暗渠”位置,正对着马府灵堂的香案。他忽然想起陈典簿的话:“祥瑞的香,藏着死人的怨。”此刻灵堂飘来的檀香里,分明混着醒魂草被烘干的焦味——那是丹毒发作时,才有的气息。
“大牛,把醒魂草塞进砖缝,”他摸向腰间的残角腰牌,断角处的“张”字刻痕,与暗渠砖面的獬豸角缺处相触,“当年我爹说过,獬豸角断处,能听死人说话。”话音未落,暗渠深处忽然传来“咔嗒”声——齿轮转动的轻响,混着骸骨摩擦的“沙沙”,像极了七年前他躲在米缸里,听见的、父母棺木被拖走的声音。
老王的烟袋锅子忽然掉进暗渠,铜锅撞击水面,惊起几只停在砖缝的蓝蝶——蝶翼上沾着的金粉,落在醒魂草叶上,竟显出“药引”二字。张金彪盯着暗渠水面的倒影,自己的残角腰牌与砖面的獬豸角,在水波里拼成完整的角,角尖指向的,是灵堂香案下的青砖——那里嵌着半枚银镯,刻着“承恩堂”的“恩”字,缺了心。
“头儿!脚夫抬的棺材在漏血!”大牛的喊声混着风雪传来,他攥着从棺材缝里抠出的粗麻布,银线獬豸纹上沾着的,不是金粉,是冻住的血珠,“这布……和您飞鱼服的补丁一样!”
张金彪忽然冲向灵堂,雪粒子打在他残角腰牌上,断角处的嫩芽银饰忽然发烫——那是母亲当年绣在襁褓上的纹样,此刻与棺材缝的银线共振,竟在雪光下,映出“张承煜”的名字。灵堂的白幡被风吹得乱晃,幡面的“祥瑞”二字被雪遮住半边,成了“亡瑞”。
“开棺。”他的声音混着风雪,砸在马府管家脸上。对方袖口的齿轮纹绣线忽然绷断,露出内侧的月牙形疤——和他掌心的,一模一样。管家后退半步,撞上香案,案上的“祥瑞纸人”摔在地上,纸页间掉出枚银针,针尖刻着“王”字,却在触地时碎成两半,露出藏在里头的血字:“第七药引,獬豸血。”
棺材盖被推开的瞬间,雪粒子灌进棺木,却没扬起半点灰尘——里头躺着的,不是马家老爷子,而是具浑身插满银针的骸骨,骸骨手腕上的银镯,刻着“张承煜”的“承”字,缺笔处嵌着醒魂草的根。张金彪忽然想起七年前母亲的血衣,衣领处的“醒”字,此刻在骸骨的指缝间显形,银线与他飞鱼服的补丁相触,竟在棺木里,拼出“醒承七载”四字。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关于提瓦特里所有女孩子都喜欢肛交这件事M
- 传承淫神技能后穿越到斗罗大陆世界莉
- 掌握催眠之力后的淫乱生活蘑
- 斗罗大陆—永恒的炮友零
- 原神 可以色色!瞳
- 幼女天空下万恶我为首
- 原神 纯粹涩涩瞳
- 斗罗淫魂z
- 斗罗大陆之超级绿牛系统枫
- 日在崩坏葉
- 斗罗:流氓篇烈
- 淫魔化的提瓦特大陆此
- 崩坏:性穹铁道tiny
- 我的美艳警察妈妈丈八蛇矛
- 用肉棒武魂打通斗罗大陆!aleXeskandar
- 原神众女涩涩风秋火儿
- 原神NTR叶
- 全面崩坏!星穹铁道!S
- 豪乳老师刘艳tttjjj_200
- 穿越到原神获得催眠系统,攻略各位美少女开后宫的故事十
- 斗破苍穹-无尽的堕落助手
- 冲喜娘妻魔师
- 崩坏星怒铁道月
- 莹妹和她的婊子伙伴们硝
- 原神众女涩涩风
- 渣夫眼瞎我选离,二嫁大佬又跪求和六焰
- 重生明末再造华夏飞星骑士2025
- 欲野垂星幻有纱雪
- 玫瑰栽培手册噫吁嚱鸭
- 四合院:掏空全院,贾家卖子求荣爱吃椒盐大虾的岳寒冬
- 天麻从白糸台开始征战全国大赛玄汐蓝
- 疯批拒做舔狗后,道侣们被拿捏了黎莫陌
- 席先生,你被太太踢出局了!九醉
- 死心后,影后前女友追悔莫及生命禁地
- 刚卷成高考状元,系统就让我躺平小鸡球球
- 一刀破仙凡大清韵
- 寡妇娘子要寻夫白玉苏苏
- 用呼吸法进行柯学网球椰奶烤茶
- 老公死了,呜呜,我装的橘铃
- 北派摸金手记大王且慢
- 如何阻止龙傲天干掉27个我松露桨
- 我不想当主角了水一天
- 说好的假结婚呢?一枝里
- 炊香满园,带着五宝种田的王妃码字怒赚两毛五
- 渣A穿进虐文爆红啦Lewin
- 我在影视城旁开饭馆一格电D
- 恶女一笑,将军折腰长白雨世
- 贬妻为妾?我二嫁权臣联手虐渣月照青松
- 八零女中医:极品小姑带娃进城了长舟渡月
- 小狗死遁后反攻了酸饺子
- 仙骨至尊锋墨汁
- 错撩温良书生后卧扇猫
- 虞妖渡一朵心闲
- [娱乐圈]我真没有恋丑癖啊鹤八
- 天降双系统砸脸,我不无敌谁无敌米利欧12138
- 我们的妻主是特种兵小鲜儿
- 乔安安小吃店[美食]三海间
- 我不想当主角了水一天
- 从一纸金章到人间真仙白云泡泡
- 婚后余生一枚柚
- 穿越之:相公你醒了!泽基山人
- 你是独属于我的帕罗西汀琉玥雀雀
- 玫瑰栽培手册噫吁嚱鸭
- 一般路过普通人会收留幽灵公安吗?揭去安眠
- 聆听夏天的秘密它的猫